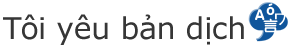- Văn bản
- Lịch sử
我是一个当了导演的观众——九把刀访谈受访:九把刀 访问:吴冠平吴:这部
我是一个当了导演的观众——九把刀访谈
受访:九把刀 访问:吴冠平
吴:这部电影是改编自你自己的小说,电影又是你做导演,你觉得你写的和拍出来的电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九:说实在的,在我的心中,忠于原著的情节是不重要的,忠于原著的精神才是最重要的。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以下简称《那些年》)这部影片中,我是编剧,同时也是导演,更是故事的亲历者,这三重身份对我来说是太好了,因为我不需要去说服什么人,告诉他这样子改编是正确的,这样子改编有没有牺牲一部分原著的精神,通常我只需要跟我自己沟通就可以。所以对我来讲,从小说到电影的转变并没有太多折中的部分,大多都是在电影节奏上的调整,没有太多的障碍。
吴:我看过一个采访,你曾说过,如果谁把你的小说买下来,你会告诉大家一个与小说不一样的结局,现在影片的结局是那个“不一样的结局”吗?
九:对!就是因为想到了这个厉害的结局,所以才决定要拍电影。我觉得任何人知道这样的结局,都会不惜代价把剧本买下来。但是同样是这个结局,因为非常珍贵,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就连主要投资人也是到签约的时候才知道,我这样做,就是要确保他们不会拿这个结局去拍另外的电影,因为小说里面没有这个结局,它有可能会被套接到别的故事上,如果是这样,我觉得非常可惜。
吴:这个“不一样的结局”是指婚礼那一段吗?
九:对,就是那一段。这个剧本在台湾得到了优良剧本奖,但是主办方有规定,得奖之后的两三个月,一定要把剧本公布在网络上。因为最初投稿的时候并没有想那么多,所以我便与主办方沟通,我不要这个奖了,奖金也悉数退还,只是不希望剧本在拍摄电影之前,就泄露这个结局。台湾的行政院还蛮有人情味,主办方只是让我签了一份同意书,在电影上映第二天,我要把这个结局公布出来,我同意了。为了保护这个结局,得不得奖都不重要了。原小说的结局到出席婚礼就结束了。小说是百分之一百的真实,它就是我的人生,对我来讲,其实不算是一个小说。原小说的叙事是讲一下过去的事情,然后时空变成现在的我正在写这个故事的情形,所以它是一个后设的故事,原小说就是一个文字的叙述,追求 100% 的真实。但电影在很多方面则需要画面上的张力。比如说男女主角吵架,我真实经历是打电话,但是这样拍就会显得非常的无趣,所以就把这个情节安排在了面对面,而且要非常视觉,要下大雨。我记得张学友有一首歌叫《分手总是在雨中》,就是这个意思。
吴:也就是说,你的朋友在看这本小说或者电影时可以对号入座。
九:对,他们在真实生活中叫什么名字,在小说里面就叫什么名字,一个字都没改。倒是在电影版本里,为了保护女主角,就改了一个字,其他人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打麻将。我选陈 希做女主角,第一时间就把陈 希的照片给他们看,他们都觉得陈 希演的这个女孩子就是当年我们追的那个女孩子的样子。
吴:这个女孩现在在哪儿?她有看到这部片子吗?
九:她跟她老公在大陆,台湾是 8 月份上映,她 6 月就到大陆了,根本来不及看。所以希望这个电影有一天可以在大陆上映,因为她是最重要的观众。
吴:看你这部片子,我个人非常亲切,就好像又回到了我的青春年代。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大陆青年人和台湾青年人的青春记忆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中学时的传纸条,如何应付考试,如何与教官斗法等等,包括上大学后,在楼道打电话那段,看着都很亲切。从青春片的角度,影片跨度很大似乎有给青春做总结的老成味。
九:因为我想要拍的是成长,青春只是故事的一个背景。从这个女孩子 17 岁拍到她 27 岁参加婚礼。其实人生很奇妙,如果你是从 27 岁到 37 岁,或者从 37 岁到 47 岁,你的感觉可能不那么明显,但如果是 17 到 27 岁,这正好是一个人格的养成,你对情感的认定,大概就是在这十年中会留一个印记在那边,什么东西会失去,什么东西会留下来,就是在 17 岁到 27 岁的中间,所以青春是必要的一部分,因为青春的很多部分是被挥霍掉的,在电影前半段表现了很多快乐的东西,后面就开始有一些遗憾和失落,而这些遗憾和失落,就是我这部片子想要拍出来的东西。
吴:我那天还在和别人聊,我觉得这部电影很难得的一点是,既能表现年轻观众的青春感,同时又能勾起我这样中年观众的怀旧感。
九:单纯要拍青春的话,其实不用这么费力把时间拉到这么远之前,应该拍现在的青春更好,因
为现在有很多流行的东西。我们的场景也不用做旧,可以省很多钱。所以这部片主要拍的不是青春。我觉得电影奇妙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时间的盒子,它可以制造出一个大家可以集体回去的时光。像电话那个东西,永远不会出现了,因为我们现在有手机。那种你要跟你喜欢的人讲话,就得排队,得珍惜,然后还要忍受被后面的人瞪你的压力。所以有些情怀就只能停留在那个时间。
吴:影片从 1994 年到 2004 年,十年间经历了很多重大的事件,最大的事件就是 1999 年台湾“9.21”大地震,我觉得无论在故事中,还是在你个人的经历中,这都是件非常事件,电影中的那段也是最感人的。这个历史节点对于你想表述的成长主题有什么样的意义?
九“:9.21”地震是台湾社会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他对每一个人来讲,记忆都不太一样。我的记忆其实是属于我个人的,而不是台湾人集体的记忆。对我来讲,那段记忆本来是非常地惊慌害怕失去重要的人,可是电话接通了,一切惊慌烟消云散。所以大地震的记忆对我来讲却是浪漫的,就是重要的人还在,也因为在这种最害怕失去重要人的时刻,你发现你自己的确抓住了什么东西,所以是很温暖的。
吴:不仅是大地震,这十年台湾经历的一些重要的文化事件,也都在片子里面出现了,这些事件似乎都影响着你的成长,形成了影片很个人化的历史观点。
九:对,回顾生命里面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是很残酷的事。那一年,政治人物做什么事情根本没有人在乎。回想过去,反而是我们听到某些歌时会想起过去的那一个自己。娱乐大明星的一些经典歌曲和事件,比如说,张国荣的去世,那些对我们来讲,反而是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时间,而不是政治。所以,影片一开始是《永远不回头》这首歌,这首歌是在很早之前,台湾非常流行的,很青春的一首歌曲,用这首歌曲来破题,然后中间又有黄舒俊的《恋爱症候群》,每个历史阶段的歌曲其实都是塞在电影里面,一直到电影最后的歌曲我用了周杰伦的《双截棍》,《双截棍》是在 2005 年才爆炸的,这其实也是我要跟观众讲,周杰伦登场了,这才是我对时代的记忆。所以《那些年》不是大事件的谱记,而是一堆生活小事件的累计。我觉得所谓电影的细节,对我来讲,就是我所喜欢的东西。我们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写完剧本,然后大家一起看,旁边的人就不免会质疑说,我们要拍一个共同记忆的东西,但为什么这个东西他没有经历过?为什么收集球员卡是重要的?我旁边的人几乎没有人收集球员卡,但我有,所以这对我是重要的。有一首婚礼上面的配乐,叫《人海中遇见你》,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听过,他们说这样不合理。你不能用一首没有人听过的歌,自以为是共同的记忆,这样子会没有共鸣.
吴:你是怎么想的?
九:我觉得,谁管你们,我的情感比较重要。所以虽然我们在拍这部影片的时候,的确是想要那种共同记忆的感觉,但是在处理上,还真的没有办法让全体的工作人员投票来决定到底应该加入什么东西。电影其实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东西,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好莱坞的那种运作模式,有非常精密的商业计算。我们都是导演一个人想“我应该做什么”,然后导演把一群人凑起来一起去拍一个电影。所以从一开始,这部电影是导演的意志作品,我根本没有去管大家的情感链接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后来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即使在影片里很多是我个人的私有经验,但是青春的情怀,永远都可以让你投射进去。这部电影在香港大卖,香港中学生的生活与台湾中学生生活怎么会一样呢?这是不合理的,但是为什么影片会这么火,不是生活方式,而是我们东方人的情感。在中学这段时间里,我们对情感的暧昧以及不敢表露心意,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这个情感界点影片是可以跨越的。甚至明明这个时空是老的,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看了,也依然可以感同身受。我们没有刻意地把大家的经验集中起来,做一个统计表,然后再决定要怎么来,我觉得这就很奇怪了。
吴:说到这,我想起片子里有一句非常打动我的话“,努力用功读书竟然可以变成这么热血的事”。你把非常个人化的动力放在一些枯燥事情的表述中,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网络创作者赋予电影的一种新趣味。
九:这部电影拍完的时候,当时没有人看好,我就敢讲话。反而电影大卖之后,我开始学着闭嘴。那时候我号称这部电影是台湾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新品种电影,说它是新品种电影,因为你不能说它是一部校园片,也不能说它是一部青春片,它总会有些突变在里面。因为有关青春的事情太个人了,台湾是导演制,所以台湾每一部关于青春的电影基本上都是导演个人对青春的诠释和理解,所以它永远都没有办法太商业化。像《蓝色大门》、《九降风》等片子,你能够明显看出一个导演是怎样活过来的。青春在他的生命里留下怎样的伤口,他就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但是我的青春时非常白痴弱智,跟学院派导演成长过程非常有差距,他们可能过去就是文艺青年,青春时比较多愁善感,就在看一些大人看的书,可能他们在青春期的时候,观察力就比我敏锐很多,所以很容易受伤,很容易沉淀一些有意义的东西,而我的青春充满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杂质,所以我拍青春的东西,跟过去的台湾导演非常不一样。我的青春是不思考的,我的思考是后来才思考,我是以后来的观点来看过去青春那些白痴的行为。我在青春的时候,确是一个没有脑袋的笨蛋,所以特别快乐是,我唯一烦恼的事就是究竟能不能够追到这个女孩子,这是当时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吴:你写小说也是为了自己这份快乐
九:那时候赚不到钱,所以肯定是为了快乐,如果一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赚到了钱,肯定就是不一样的结局了。
吴:你最初开始写网络小说的时候,都喜欢写哪些事?
九:一开始就是天马行空,特别喜欢写那些惊悚恐怖类型的小说,直到五年之后才开始写自己的故事。如果是赚钱,一开始就应该写爱情小说,它永远是最受欢迎的类型,这个也完全可以理解,所有人最想追求的就是爱情。那时候的我很快乐,因为我还是一个学生,在我的脑袋里面,读书是兴趣,写小说才是正职,同时学生的身份也保护了我,不被社会瞧不起,也没有父母的压力。我赚一点钱,可以买很多东西,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相当富有,但是以社会人士的标准来看,那简直是贫穷到了不行。在学生身份结束的那一年,正好小说大卖,一切走上正轨,所以我真的非常幸运。
吴:你觉得成长和爱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九:我可能永远都弄不太明白,因为,男生会思考这些问题,都是被女生逼的。爱不爱,男生根本不会去思考。文艺男青年也许会思考,但我不是,喜欢女生是非常直接的事情。比如初恋,我不觉得小学时候喜欢一个女孩子可以称为初恋,如果是这样子,每个人的初恋都会非常早。如果下一个比较精准的定义就是,第一个在你心里留下伤口的人那可以成为你的初恋。因为爱情有很多种方式,如果非要有一个完整课程的话,目送恋人的背影离开便是爱情的最后一堂课,不管是你甩别人还是别人甩你;而留下的那道伤口是第一堂课,过好几年才知道痛。一道伤口,当下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反正青春还很长,我们常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可是我觉得这句话是为那些不懂珍惜的人而说的。我常常想,如果一段感情你十年之后都不会在乎,那现在也不需要为这件事情而生气了。爱情,回首十年如果是痛苦的,那是因为心中对曾经的伤痛与背叛依然无法释怀。成长,如果只是告诉我你要放下这一切,过去终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那我不要这样!成长不应该告诉我,爱情永远都会失而复得,永远可以更美好,不是!任何一份爱情都没有办法被抹去,也许我们彼此会遇到另外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没有谁可以取代曾经的她(他)!所以成长告诉我,没有一份爱情会完整复原,要珍惜这个人。这是一部有旁白的电影,旁白为这部电影多了一个观点、一个视角,这个视角便是多年之后我回首看这一段青春的视角。同时,旁白也是电影里的另外一个灵魂。他提供了怀旧的空间,提供了长大的角度,是一段长大的自己与年轻的自己的对话,这才是所谓的成长。我一直很抗拒“我们要放下才可以前进”这个观点,我放不下才拍了这部电影,我太想珍惜过去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为什么要放下它,不如统统扛起来,一起前进。
吴
0/5000
我是一个当了导演的观众 — — 九把刀访谈受访:九把刀 访问:吴冠平吴:这部电影是改编自你自己的小说, 电影又是你做导演, 你觉得你写的和拍出来的电影,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九:说实在的, 在我的心中, 忠于原著的情节是不重要的, 忠于原著的精神才是最重要的。 在《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以下简称《那些年》) 这部影片中, 我是编剧, 同时也是导演, 更是故事的亲历者, 这三重身份对我来说是太好了, 因为我不需要去说服什么人, 告诉他这样子改编是正确的, 这样子改编有没有牺牲一部分原著的精神, 通常我只需要跟我自己沟通就可以。 所以对我来讲, 从小说到电影的转变并没有太多折中的部分, 大多都是在电影节奏上的调整, 没有太多的障碍。吴:我看过一个采访, 你曾说过, 如果谁把你的小说买下来, 你会告诉大家一个与小说不一样的结局, 现在影片的结局是那个 "不一样的结局" 吗?九:对! 就是因为想到了这个厉害的结局, 所以才决定要拍电影。 我觉得任何人知道这样的结局, 都会不惜代价把剧本买下来。 但是同样是这个结局, 因为非常珍贵,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甚至就连主要投资人也是到签约的时候才知道, 我这样做, 就是要确保他们不会拿这个结局去拍另外的电影, 因为小说里面没有这个结局, 它有可能会被套接到别的故事上, 如果是这样, 我觉得非常可惜。吴:这个 "不一样的结局" 是指婚礼那一段吗?九:对, 就是那一段。 这个剧本在台湾得到了优良剧本奖, 但是主办方有规定, 得奖之后的两三个月, 一定要把剧本公布在网络上。 因为最初投稿的时候并没有想那么多, 所以我便与主办方沟通, 我不要这个奖了, 奖金也悉数退还, 只是不希望剧本在拍摄电影之前, 就泄露这个结局。 台湾的行政院还蛮有人情味, 主办方只是让我签了一份同意书, 在电影上映第二天, 我要把这个结局公布出来, 我同意了。 为了保护这个结局, 得不得奖都不重要了。 原小说的结局到出席婚礼就结束了。 小说是百分之一百的真实, 它就是我的人生, 对我来讲, 其实不算是一个小说。 原小说的叙事是讲一下过去的事情, 然后时空变成现在的我正在写这个故事的情形, 所以它是一个后设的故事, 原小说就是一个文字的叙述, 追求 100% 的真实。 但电影在很多方面则需要画面上的张力。 比如说男女主角吵架, 我真实经历是打电话, 但是这样拍就会显得非常的无趣, 所以就把这个情节安排在了面对面, 而且要非常视觉, 要下大雨。 我记得张学友有一首歌叫《分手总是在雨中》, 就是这个意思。吴:也就是说, 你的朋友在看这本小说或者电影时可以对号入座。九:对,他们在真实生活中叫什么名字,在小说里面就叫什么名字,一个字都没改。倒是在电影版本里,为了保护女主角,就改了一个字,其他人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打麻将。我选陈 希做女主角,第一时间就把陈 希的照片给他们看,他们都觉得陈 希演的这个女孩子就是当年我们追的那个女孩子的样子。吴:这个女孩现在在哪儿?她有看到这部片子吗?九:她跟她老公在大陆,台湾是 8 月份上映,她 6 月就到大陆了,根本来不及看。所以希望这个电影有一天可以在大陆上映,因为她是最重要的观众。吴:看你这部片子,我个人非常亲切,就好像又回到了我的青春年代。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大陆青年人和台湾青年人的青春记忆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中学时的传纸条,如何应付考试,如何与教官斗法等等,包括上大学后,在楼道打电话那段,看着都很亲切。从青春片的角度,影片跨度很大似乎有给青春做总结的老成味。九:因为我想要拍的是成长,青春只是故事的一个背景。从这个女孩子 17 岁拍到她 27 岁参加婚礼。其实人生很奇妙,如果你是从 27 岁到 37 岁,或者从 37 岁到 47 岁,你的感觉可能不那么明显,但如果是 17 到 27 岁,这正好是一个人格的养成,你对情感的认定,大概就是在这十年中会留一个印记在那边,什么东西会失去,什么东西会留下来,就是在 17 岁到 27 岁的中间,所以青春是必要的一部分,因为青春的很多部分是被挥霍掉的,在电影前半段表现了很多快乐的东西,后面就开始有一些遗憾和失落,而这些遗憾和失落,就是我这部片子想要拍出来的东西。吴:我那天还在和别人聊,我觉得这部电影很难得的一点是,既能表现年轻观众的青春感,同时又能勾起我这样中年观众的怀旧感。九:单纯要拍青春的话,其实不用这么费力把时间拉到这么远之前,应该拍现在的青春更好,因为现在有很多流行的东西。我们的场景也不用做旧,可以省很多钱。所以这部片主要拍的不是青春。我觉得电影奇妙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时间的盒子,它可以制造出一个大家可以集体回去的时光。像电话那个东西,永远不会出现了,因为我们现在有手机。那种你要跟你喜欢的人讲话,就得排队,得珍惜,然后还要忍受被后面的人瞪你的压力。所以有些情怀就只能停留在那个时间。吴:影片从 1994 年到 2004 年,十年间经历了很多重大的事件,最大的事件就是 1999 年台湾“9.21”大地震,我觉得无论在故事中,还是在你个人的经历中,这都是件非常事件,电影中的那段也是最感人的。这个历史节点对于你想表述的成长主题有什么样的意义?九“:9.21”地震是台湾社会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他对每一个人来讲,记忆都不太一样。我的记忆其实是属于我个人的,而不是台湾人集体的记忆。对我来讲,那段记忆本来是非常地惊慌害怕失去重要的人,可是电话接通了,一切惊慌烟消云散。所以大地震的记忆对我来讲却是浪漫的,就是重要的人还在,也因为在这种最害怕失去重要人的时刻,你发现你自己的确抓住了什么东西,所以是很温暖的。吴:不仅是大地震,这十年台湾经历的一些重要的文化事件,也都在片子里面出现了,这些事件似乎都影响着你的成长,形成了影片很个人化的历史观点。九:对,回顾生命里面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是很残酷的事。那一年,政治人物做什么事情根本没有人在乎。回想过去,反而是我们听到某些歌时会想起过去的那一个自己。娱乐大明星的一些经典歌曲和事件,比如说,张国荣的去世,那些对我们来讲,反而是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时间,而不是政治。所以,影片一开始是《永远不回头》这首歌,这首歌是在很早之前,台湾非常流行的,很青春的一首歌曲,用这首歌曲来破题,然后中间又有黄舒俊的《恋爱症候群》,每个历史阶段的歌曲其实都是塞在电影里面,一直到电影最后的歌曲我用了周杰伦的《双截棍》,《双截棍》是在 2005 年才爆炸的,这其实也是我要跟观众讲,周杰伦登场了,这才是我对时代的记忆。所以《那些年》不是大事件的谱记,而是一堆生活小事件的累计。我觉得所谓电影的细节,对我来讲,就是我所喜欢的东西。我们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写完剧本,然后大家一起看,旁边的人就不免会质疑说,我们要拍一个共同记忆的东西,但为什么这个东西他没有经历过?为什么收集球员卡是重要的?我旁边的人几乎没有人收集球员卡,但我有,所以这对我是重要的。有一首婚礼上面的配乐,叫《人海中遇见你》,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听过,他们说这样不合理。你不能用一首没有人听过的歌,自以为是共同的记忆,这样子会没有共鸣.吴:你是怎么想的?九:我觉得,谁管你们,我的情感比较重要。所以虽然我们在拍这部影片的时候,的确是想要那种共同记忆的感觉,但是在处理上,还真的没有办法让全体的工作人员投票来决定到底应该加入什么东西。电影其实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东西,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好莱坞的那种运作模式,有非常精密的商业计算。我们都是导演一个人想“我应该做什么”,然后导演把一群人凑起来一起去拍一个电影。所以从一开始,这部电影是导演的意志作品,我根本没有去管大家的情感链接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后来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即使在影片里很多是我个人的私有经验,但是青春的情怀,永远都可以让你投射进去。这部电影在香港大卖,香港中学生的生活与台湾中学生生活怎么会一样呢?这是不合理的,但是为什么影片会这么火,不是生活方式,而是我们东方人的情感。在中学这段时间里,我们对情感的暧昧以及不敢表露心意,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这个情感界点影片是可以跨越的。甚至明明这个时空是老的,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看了,也依然可以感同身受。我们没有刻意地把大家的经验集中起来,做一个统计表,然后再决定要怎么来,我觉得这就很奇怪了。吴:说到这,我想起片子里有一句非常打动我的话“,努力用功读书竟然可以变成这么热血的事”。你把非常个人化的动力放在一些枯燥事情的表述中,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网络创作者赋予电影的一种新趣味。
九:这部电影拍完的时候,当时没有人看好,我就敢讲话。反而电影大卖之后,我开始学着闭嘴。那时候我号称这部电影是台湾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新品种电影,说它是新品种电影,因为你不能说它是一部校园片,也不能说它是一部青春片,它总会有些突变在里面。因为有关青春的事情太个人了,台湾是导演制,所以台湾每一部关于青春的电影基本上都是导演个人对青春的诠释和理解,所以它永远都没有办法太商业化。像《蓝色大门》、《九降风》等片子,你能够明显看出一个导演是怎样活过来的。青春在他的生命里留下怎样的伤口,他就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但是我的青春时非常白痴弱智,跟学院派导演成长过程非常有差距,他们可能过去就是文艺青年,青春时比较多愁善感,就在看一些大人看的书,可能他们在青春期的时候,观察力就比我敏锐很多,所以很容易受伤,很容易沉淀一些有意义的东西,而我的青春充满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杂质,所以我拍青春的东西,跟过去的台湾导演非常不一样。我的青春是不思考的,我的思考是后来才思考,我是以后来的观点来看过去青春那些白痴的行为。我在青春的时候,确是一个没有脑袋的笨蛋,所以特别快乐是,我唯一烦恼的事就是究竟能不能够追到这个女孩子,这是当时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吴:你写小说也是为了自己这份快乐
九:那时候赚不到钱,所以肯定是为了快乐,如果一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赚到了钱,肯定就是不一样的结局了。
吴:你最初开始写网络小说的时候,都喜欢写哪些事?
九:一开始就是天马行空,特别喜欢写那些惊悚恐怖类型的小说,直到五年之后才开始写自己的故事。如果是赚钱,一开始就应该写爱情小说,它永远是最受欢迎的类型,这个也完全可以理解,所有人最想追求的就是爱情。那时候的我很快乐,因为我还是一个学生,在我的脑袋里面,读书是兴趣,写小说才是正职,同时学生的身份也保护了我,不被社会瞧不起,也没有父母的压力。我赚一点钱,可以买很多东西,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相当富有,但是以社会人士的标准来看,那简直是贫穷到了不行。在学生身份结束的那一年,正好小说大卖,一切走上正轨,所以我真的非常幸运。
吴:你觉得成长和爱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九:我可能永远都弄不太明白,因为,男生会思考这些问题,都是被女生逼的。爱不爱,男生根本不会去思考。文艺男青年也许会思考,但我不是,喜欢女生是非常直接的事情。比如初恋,我不觉得小学时候喜欢一个女孩子可以称为初恋,如果是这样子,每个人的初恋都会非常早。如果下一个比较精准的定义就是,第一个在你心里留下伤口的人那可以成为你的初恋。因为爱情有很多种方式,如果非要有一个完整课程的话,目送恋人的背影离开便是爱情的最后一堂课,不管是你甩别人还是别人甩你;而留下的那道伤口是第一堂课,过好几年才知道痛。一道伤口,当下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反正青春还很长,我们常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可是我觉得这句话是为那些不懂珍惜的人而说的。我常常想,如果一段感情你十年之后都不会在乎,那现在也不需要为这件事情而生气了。爱情,回首十年如果是痛苦的,那是因为心中对曾经的伤痛与背叛依然无法释怀。成长,如果只是告诉我你要放下这一切,过去终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那我不要这样!成长不应该告诉我,爱情永远都会失而复得,永远可以更美好,不是!任何一份爱情都没有办法被抹去,也许我们彼此会遇到另外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没有谁可以取代曾经的她(他)!所以成长告诉我,没有一份爱情会完整复原,要珍惜这个人。这是一部有旁白的电影,旁白为这部电影多了一个观点、一个视角,这个视角便是多年之后我回首看这一段青春的视角。同时,旁白也是电影里的另外一个灵魂。他提供了怀旧的空间,提供了长大的角度,是一段长大的自己与年轻的自己的对话,这才是所谓的成长。我一直很抗拒“我们要放下才可以前进”这个观点,我放不下才拍了这部电影,我太想珍惜过去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为什么要放下它,不如统统扛起来,一起前进。
吴
九:这部电影拍完的时候,当时没有人看好,我就敢讲话。反而电影大卖之后,我开始学着闭嘴。那时候我号称这部电影是台湾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新品种电影,说它是新品种电影,因为你不能说它是一部校园片,也不能说它是一部青春片,它总会有些突变在里面。因为有关青春的事情太个人了,台湾是导演制,所以台湾每一部关于青春的电影基本上都是导演个人对青春的诠释和理解,所以它永远都没有办法太商业化。像《蓝色大门》、《九降风》等片子,你能够明显看出一个导演是怎样活过来的。青春在他的生命里留下怎样的伤口,他就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但是我的青春时非常白痴弱智,跟学院派导演成长过程非常有差距,他们可能过去就是文艺青年,青春时比较多愁善感,就在看一些大人看的书,可能他们在青春期的时候,观察力就比我敏锐很多,所以很容易受伤,很容易沉淀一些有意义的东西,而我的青春充满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杂质,所以我拍青春的东西,跟过去的台湾导演非常不一样。我的青春是不思考的,我的思考是后来才思考,我是以后来的观点来看过去青春那些白痴的行为。我在青春的时候,确是一个没有脑袋的笨蛋,所以特别快乐是,我唯一烦恼的事就是究竟能不能够追到这个女孩子,这是当时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吴:你写小说也是为了自己这份快乐
九:那时候赚不到钱,所以肯定是为了快乐,如果一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赚到了钱,肯定就是不一样的结局了。
吴:你最初开始写网络小说的时候,都喜欢写哪些事?
九:一开始就是天马行空,特别喜欢写那些惊悚恐怖类型的小说,直到五年之后才开始写自己的故事。如果是赚钱,一开始就应该写爱情小说,它永远是最受欢迎的类型,这个也完全可以理解,所有人最想追求的就是爱情。那时候的我很快乐,因为我还是一个学生,在我的脑袋里面,读书是兴趣,写小说才是正职,同时学生的身份也保护了我,不被社会瞧不起,也没有父母的压力。我赚一点钱,可以买很多东西,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相当富有,但是以社会人士的标准来看,那简直是贫穷到了不行。在学生身份结束的那一年,正好小说大卖,一切走上正轨,所以我真的非常幸运。
吴:你觉得成长和爱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九:我可能永远都弄不太明白,因为,男生会思考这些问题,都是被女生逼的。爱不爱,男生根本不会去思考。文艺男青年也许会思考,但我不是,喜欢女生是非常直接的事情。比如初恋,我不觉得小学时候喜欢一个女孩子可以称为初恋,如果是这样子,每个人的初恋都会非常早。如果下一个比较精准的定义就是,第一个在你心里留下伤口的人那可以成为你的初恋。因为爱情有很多种方式,如果非要有一个完整课程的话,目送恋人的背影离开便是爱情的最后一堂课,不管是你甩别人还是别人甩你;而留下的那道伤口是第一堂课,过好几年才知道痛。一道伤口,当下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反正青春还很长,我们常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可是我觉得这句话是为那些不懂珍惜的人而说的。我常常想,如果一段感情你十年之后都不会在乎,那现在也不需要为这件事情而生气了。爱情,回首十年如果是痛苦的,那是因为心中对曾经的伤痛与背叛依然无法释怀。成长,如果只是告诉我你要放下这一切,过去终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那我不要这样!成长不应该告诉我,爱情永远都会失而复得,永远可以更美好,不是!任何一份爱情都没有办法被抹去,也许我们彼此会遇到另外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没有谁可以取代曾经的她(他)!所以成长告诉我,没有一份爱情会完整复原,要珍惜这个人。这是一部有旁白的电影,旁白为这部电影多了一个观点、一个视角,这个视角便是多年之后我回首看这一段青春的视角。同时,旁白也是电影里的另外一个灵魂。他提供了怀旧的空间,提供了长大的角度,是一段长大的自己与年轻的自己的对话,这才是所谓的成长。我一直很抗拒“我们要放下才可以前进”这个观点,我放不下才拍了这部电影,我太想珍惜过去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为什么要放下它,不如统统扛起来,一起前进。
吴
đang được dịch, vui lòng đợi..


我是一个当了导演的观众-访谈九把刀
受访:九把刀 100% 希做女主角,第一时间就把陈希的照片给他们看,他们都觉得陈 8月份上映,她6 17岁拍到她27岁参加婚礼.其实人生很奇妙,如果你是从27岁到37岁,或者从37岁到47岁,你的感觉可能不那么明显,但如果是17到27 17岁到27 1994年到2004年,十年间经历了很多重大的事件,最大的事件就是1999 2005
đang được dịch, vui lòng đợi..


Các ngôn ngữ khác
Hỗ trợ công cụ dịch thuật: Albania, Amharic, Anh, Armenia, Azerbaijan, Ba Lan, Ba Tư, Bantu, Basque, Belarus, Bengal, Bosnia, Bulgaria, Bồ Đào Nha, Catalan, Cebuano, Chichewa, Corsi, Creole (Haiti), Croatia, Do Thái, Estonia, Filipino, Frisia, Gael Scotland, Galicia, George, Gujarat, Hausa, Hawaii, Hindi, Hmong, Hungary, Hy Lạp, Hà Lan, Hà Lan (Nam Phi), Hàn, Iceland, Igbo, Ireland, Java, Kannada, Kazakh, Khmer, Kinyarwanda, Klingon, Kurd, Kyrgyz, Latinh, Latvia, Litva, Luxembourg, Lào, Macedonia, Malagasy, Malayalam, Malta, Maori, Marathi, Myanmar, Mã Lai, Mông Cổ, Na Uy, Nepal, Nga, Nhật, Odia (Oriya), Pashto, Pháp, Phát hiện ngôn ngữ, Phần Lan, Punjab, Quốc tế ngữ, Rumani, Samoa, Serbia, Sesotho, Shona, Sindhi, Sinhala, Slovak, Slovenia, Somali, Sunda, Swahili, Séc, Tajik, Tamil, Tatar, Telugu, Thái, Thổ Nhĩ Kỳ, Thụy Điển, Tiếng Indonesia, Tiếng Ý, Trung, Trung (Phồn thể), Turkmen, Tây Ban Nha, Ukraina, Urdu, Uyghur, Uzbek, Việt, Xứ Wales, Yiddish, Yoruba, Zulu, Đan Mạch, Đức, Ả Rập, dịch ngôn ngữ.
- Tất cả đều có giấy kiểm định chất so
- A zero-sum or constant-sum game is one i
- say đắm
- sau đây, tôi sẽ kể lại một câu chuyê
- 好,他證實了兩人已經分手的消息。 一週精彩娛樂 秦嵐在部落格上透露分手 日前,某
- sau đây, tôi sẽ kể lại một câu chuyê
- 好,他證實了兩人已經分手的消息。 一週精彩娛樂 秦嵐在部落格上透露分手 日前,某
- that is all of our selection
- 9. While the quality of facilities have
- 捉え方
- hương hoa
- advertisements
- Ngoài ra bài báo cũng chỉ ra EmotionSens
- Does anybody here Are a seller
- pay attentiongeneral
- Mua
- This year, humanity dared to take bold s
- phương trình phản ứng
- This year, humanity dared to take bold s
- Ngoài ra bài báo cũng chỉ ra EmotionSens
- 【只要 火影披风】 【火影披风+送戒指】 【火影披风+送护额】 【火影披风+戒指
- anh mua bia có giao tại nhà không
- I want to hear your voice
- Jim is fond of doing researchscientifica